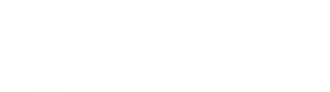“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大學是從事教學科研的學術機構,應該恢復以學術為主導的管理體制。梅蘭芳的劇團只能由梅蘭芳主導才能辦好,大學也只能由骨干教授的集體主導才能辦好。不同學校的骨干教授主導的方式可能不盡相同,這樣就會形成學校的真正特色。” ——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校長 朱清時 30多年前我國開始改革開放,我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1979年我被公派赴美國進修,回國后先在中科院做專業科研,1994年以后又從事教育,并在1998—2008年做了10年中國科大校長。30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進行教育改革,我的認識經過了三個階段,看到了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層次,我對比在國外工作的經驗,感覺我國的高等教育水平與世界一流差距甚大,是因為我們的課程體系不行,教材內容陳舊,灌輸式教學方法不利于學生素質和能力的培養。所以我做校長以后,就組織人員到全世界各地去調研,回來編寫新大綱和新教材,并進行教學方法的改革。開始進行得還好,后來卻推行不下去了,因為教師們缺乏內在的積極性,諸事很快就流于形式。世界一流大學,如哈佛、牛津、劍橋,很少有人談創新教育,但所做之事卻總很創新。由此我認識到,課程體系和教材,乃至教學方法,都只是技術問題,是浮在表面的現象,當然也都很重要,但教改必須抓住深層次的問題才行。 第二階段我覺得,人才是關鍵,大學有了好的師資隊伍,教學改革才能做好。沒有好的人才,好事可能流于形式,好經也可能被念歪。于是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引進人才上。近年來,中科大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樣,每年都從海外引進一些教授或副教授,現在我國重點大學的教師隊伍已經煥然一新,然而教改卻仍無明顯進展。這時我才發現,引進的人才回來后,思想和行為方式就漸漸發生變化,例如他們在國內參加學術交流,很快就拋棄了國際學術界讓年輕人唱主角的優良傳統,也習慣于讓“大腕”做大報告。不是因為“大腕”們有真知灼見,而是因為他們身份地位高。大家已不在意交流新思想,而是崇拜權力和地位。這樣一來他們的創新能力在退步,真如古語所道“南橘北枳”。這說明教育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在“土壤”,即管理體制之中。 第三階段我認識到,我們的大學管理體制已“行政化”, 即大學被當成行政機構來管理。我們的學校領導人都是上級任命的官員,靠行政權力治校,下級服從上級。教授們沒有話語權,只能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去做官。于是產生了大家不去競爭學術好,而是崇尚權力大、地位高的校園文化。在這種氛圍中學術就萎縮了。 我國農村也曾是高度行政化,行政權力干預農業生產,結果農業搞得不理想。30年前的農村改革實際上就是“去行政化”,讓農民自己來決定種什么,怎么種,農業就恢復了生機。農村改革為我國的經濟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教育的現狀跟改革之前的農業一樣,沒有活力,主要不是因為我們的經費不夠,甚至也不是由于我們的課程體系不行,而是不恰當的管理體制使教授發揮不了聰明才智,就像過去農民發揮不了作用一樣。因此當前我國教改的根本問題是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要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學校的管理體制扭回到學術主導的狀態。不要只在那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修修補補。 過去的梅蘭芳劇團,它的社會功能只是唱好戲,因此管理體制圍繞讓梅蘭芳唱好戲來運轉,梅蘭芳起主導作用,于是梅蘭芳劇團成為了藝術史上的奇葩。與它同時的還有馬連良劇團、尚小云劇團等,真正是“百花齊放”。后來這些劇團都被行政化了,其戲劇藝術也就凋零了。學校的社會定位本是一個從事教學和科研的學術機構,管理體制應該“學術優先,學者主導”。如果不切實際地賦予它許多其他功能,由一些官員用行政權力來主導,它們就會失去活力。 因此,要對我國的教育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從學校的管理制度,特別是干部制度改革做起。建議組織部門總結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制定出“學術機構領導干部任用辦法”,適用于學校、科研院所、劇團等學術機構。這并不是說組織部門現行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問題,只是說社會上各類機構千差萬別,不能只用一套統一的辦法來管理。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大學是從事教學科研的學術機構,應該恢復以學術為主導的管理體制。梅蘭芳劇團只能由梅蘭芳主導才能辦好,大學也只能由骨干教授的集體主導才能辦好。不同學校的骨干教授主導的方式可能不盡相同,這樣就會形成學校的真正特色。 有人會擔心這樣的學校在政治方向上出問題,這沒必要。30多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時,曾有人這樣擔心過,然而歷史已經做了結論。我們國家不僅未出問題,而且反而比當初更強大。今后30年我國的改革中,教育改革是至關重要的領域,在管理體制上“殺出一條血路”,這樣的教改成功了,我們才可能成為人才強國,中華民族才會真正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