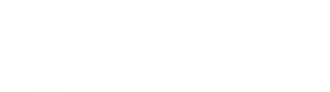《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近日發布,調查結果顯示,59.2%的女大學生愿意嫁給“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奮斗很多年,超過總數的一半。盡管調查結果還顯示,有57.6%的女大學生愿意選擇“潛力股”結婚對象,但人們似乎對近六成女大學生愿嫁“富二代”這一結果更感興趣。于是,質疑、指責者不在少數,同情、鼓勵者也有不少。59.2%,能說明什么?如何看待大學生的婚戀觀? “愿嫁”也無奈 女大學生不忙求職忙征婚,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這不是逃避現實,拿青春賭明天,褻瀆自己的幸福? 客觀地講,“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確實對女大學生產生了一定的誤導。社會提醒女大學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達到事業家庭雙豐收,對女大學生具有勵志意義。但是換個角度看,在不容樂觀的就業現實面前,大學生希望嫁“富二代”也是一種趨利避害的現實利益訴求。 現代社會,誰不愿意自立自強,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顯身手?誰愿意寄人籬下,以嫁“富二代”傍大款的形式來詮釋上大學的價值?我相信,每位女生都希望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發展屬于自己的事業,誰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幸福與前途開玩笑。但是就業崗位僧多粥少,大學生調低就業期望值,不斷嘗試,無可指責。 面對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的調查結果,一方面,女大學生要反思人生定位,打破功利思維,學會自立自強;政府、社會、學校要引導她們樹立積極的就業觀和婚姻觀;另一方面,我們不妨拋棄對或錯的觀念,把愿嫁“富二代”理解為個人的一種生活選擇,對此予以寬容。文/劉凱玲 最近幾年,“富二代”一詞有被標簽化傾向。在一些人眼里,一提“富二代”,似乎就等同于“紈绔子弟”和“豪放小姐”。實際上,這是不科學、不公平的。絕大多數的“富二代”并不是人們想像的那個樣子。相反,他們大多數是為人謙虛低調,遵紀守法,積極向上的。所以,不要帶著“有色眼鏡”,不要把“富二代”等同于一個貶義詞。 其實,“富二代”到目前為止,還僅僅是一種口語化的表達,還沒有嚴格的標準與定義,更不用說社會共識了。幾十年前,我們講“富”,是以“萬元戶”為標志的。有專家測算,按照人均貨幣收入或者城鎮職工平均工資來看,30年前的1萬元,大體相當于現在的近30萬元。如果以此為標準確立的“富二代”,則沒有任何的社會學意義,不具有研究價值。那么,究竟父母擁有多少財富的子女才算得上“富二代”?100萬,還是1000萬,是人民幣,還是美元?沒有標準,就沒有歸類對象。就如一千個觀眾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在不同女大學生眼中的“富二代”,有不同的標準,59.2%這個數字根本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雖然愿嫁“富二代”是個偽問題,但在當今社會,大學生的婚戀觀務實化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婚戀觀走出柏拉圖精神之戀,走出“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的想象之戀,不僅不是什么壞事,而是好事。然而,“一枚硬幣總有兩面”,少數女性受到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影響,“傍大款”、“當二奶”。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潮也有抬頭的趨勢。這種社會影響滲透到校園,加上當前大學生就業壓力大,崗位競爭激烈,社會向上流動通道不暢等原因,使得大學生的婚戀觀也進一步社會化、世俗化,出現了所謂的“畢婚族”、“急婚族”,以及有了“嫁富二代”、“少奮斗幾十年”的想法。 女大學生希望嫁得好,太正常不過了。但是不是嫁“富”就等于“嫁得好”,則是可以商榷、引導的。我們不鼓勵女大學生都嫁“富”,但也不希望女大學都嫁“窮”。如何讓嫁“富”與嫁“窮”自然融合呢?除了學校的婚戀觀教育之外,改革社會財富的分配機制,暢通社會流動通道,實現共同富裕,才是根本之策。 文/郭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