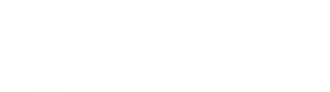“曾遇批評,讓我下臺” 新京報:你曾被學生怎樣批評?最尖銳的批評是什么? 李培根:各方面的批評。最尖銳的一次,我記得是我們文華學院的學位門事件。(文華學院是華中科技大學的一個二級學院。2007年,該學院1300名畢業生中有超過700人拿到了“華中大”的文憑,而以前這個學院沒有那么多學生能拿到主校的文憑。有學生便認為“華中大”在買賣文憑。) 當時網上有一個帖子,尖銳到什么程度,內容是“把這個爛人李培根揪下臺,如有問題,把他雙規。” 新京報:看到帖子后是什么感覺? 李培根:看到一笑。我感到很好笑,沒什么。這么多學生中,有那么幾個學生偏激一點,沒有什么大驚小怪。 新京報:你是怎么處理學生對學位門事件的質疑? 李培根:學校召開了一個見面會。當時我回應說,我校嚴格在國家政策允許范圍內行事。其實有些批評是學生不了解全面的情況。真誠面對學生了、解釋了,就好了。 新京報:校方領導的意見一致嗎?都能和你一樣真誠面對學生嗎? 李培根:學校的高層是有異議,部分同志希望不要去解釋,他們覺得越講越不清楚,把問題弄得更復雜,對學校不好。我的想法是,既然學生有那么大的意見,作為學校來講,有道理,得面對;沒道理,也得面對。 新京報:你不擔心出面后會下不了臺? 李培根:只要是真誠面對學生,學生為什么會不理解呢?如果這個事情學校的確是有失誤,學校應該坦言,學生會接受;如果是學生不了解全面情況,只看到一方面,你真誠面對的話,學生也能夠理解。 新京報:你出面后,學生情緒平息了嗎? 李培根:基本平息了。 “和學生溝通,還不理想” 新京報:學位門事件后,“華中大”每學期都召開兩次見面會。是出于什么考慮,把見面制度化? 李培根:我希望學校要有一個保持學生和學校方方面面正常的溝通渠道。盡管到現在為止,這個渠道不一定建立好了,可能還并不理想。但我們還在朝這方面努力。 新京報:學生有個普遍印象是,似乎每次只有你出面回應,學校其他的職能部門并沒有出面。 李培根:那顯然是很不好的。 新京報:學生們更關心的也許不是你表態了,而是這件事情能否得到最終解決。但職能部門如果不面對,是否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李培根:所以我們學生對我也有不滿意的,這也是我的一個問題。有時候我跟學生講起來一件事情,聽著蠻好的,但在他們看來,好像跟我講的差距太大了。 新京報:什么差距?能舉個例子嗎? 李培根:比如我在演講中說,學校絕不賺學生的一分錢,我也知道學生對食堂并不滿意。那我說的是不是假話呢?不是,我說的肯定是心里話。但學生覺得學校沒做到這一點。我相信有部分是食堂做得不好;后勤也有一定的困難,他們也盡了全力。但學生也沒有全面了解情況。 新京報:你認為學生和校方之間的理想溝通應該是怎樣的? 李培根:“以學生為本”的觀念真正深入到管理干部和教師當中,深入到職能部門中去,才是理想的溝通。 新京報:推進這種理想的溝通時,你會有一種無力感嗎? 李培根:比如食堂這件事,我也經常跟后勤的人打招呼,他們其實也盡了力,但如果真的要求后勤的每個人都做到心里裝著學生,這也是不現實的。 “我給自己打70分” 新京報:畢業典禮上,有那么多學生愛戴你,你從2005年任職至今,給“華中大”帶來哪些改變? 李培根:改變肯定有一些,但我不滿意。 新京報:在你任職期間,你會給“華中大”打多少分? 李培根:整個學校的情況,應該是及格吧。 新京報:那你會給做校長的自己打多少分? 李培根:70分。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的“華中大”有哪些不足? 李培根: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我們講的“以學生為本”。講是很好講,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這一點來打分的話,我都懷疑能不能打及格。 新京報:你認為“華中大”還沒有做到以“學生為本”? 李培根:應該說以學生為本沒有真正深入到大面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離更大了。 新京報:怎么理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離更大了”? 李培根:大多數教師在上課之外,跟學生的接觸太少。我在國外念書時,教授上課是上課的時間,另外還有一個專門接待學生的時間,你可以去辦公室跟他討論。 新京報:國內的大學教授課后都忙于什么? 李培根:忙于一些功利的事情。當然,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教職工。如果教師的收入完全只依靠工資的話,教師早就都跑掉了。 新京報:但為什么社會普遍認為大學教授的整體收入不低? 李培根:雖然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還得體,但是那要通過類似于創收的活動來取得。僅工資收入并不高,大學一級教師(即院士級別)的工資收入——院士,每個月是2800元。這就使得老師需要更多地去考慮怎樣增加津貼和獎金,肯定會減少關注學生的程度。 新京報:“華中大”是否嘗試讓教師多關注現學生,如設置課后“學生接待日”? 李培根:有嘗試,但就“華中大”整體而言,還沒做到。 新京報:為什么改變那么難? 李培根:這個是現實。作為校長,不能說:你們在學校里頭只能拿這么點工資,不能干別的。這是做不到的。目前如果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是個很大的系統,需要國家加大教育投入,使得老師不把精力放在創收上。而這不是一個學校的校長可以解決的。 “我講真話,但不是異類” 新京報:那么多學生喜歡你,是否意味著你是一名成功的校長? 李培根:千萬不能這么講。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成功的校長。自己更多的是要看到問題的一面,不能陶醉在成績里。 新京報:從你的演講稿來看,你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的人。 李培根:應該是。我本質上是一個善于思考善于學習的人。 新京報:也聽說,有時候你在外邊說話,“華中大”宣傳部工作人員會提心吊膽,為什么? 李培根:我能理解他們,他們搞宣傳的人會比較謹慎。 新京報:他們怕你亂說話? 李培根:我只是不喜歡講假話。我不敢說我把所有的真話都講出來了,但我講的都是真話。 新京報:你認為講真話的校長算是異類嗎? 李培根:我相信很多校長都講真話。我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校長了。 新京報:作為一個教育管理者,很多時候無法實現理想,你還會喜歡這個職業嗎? 李培根:喜歡。不喜歡的事,別人無法強迫。 新京報:什么地方吸引你? 李培根:大學教授影響的只是很小的一個點,那就是做好自己的學問。而校長,畢竟有可能去影響更大的范圍。 “高校小一點更好” 新京報:你曾說,影響一個大學的聲譽的最重要因素是這個大學的校友在社會上的總體表現。為什么這么說? 李培根:你心目中最好的大學,是因為記住了它發表了多少文章,獲得多少獎嗎?不是的。北大、清華好,是因為很多有杰出表現的是北大清華人。所以,對學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學生們在校期間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使得他們今后有更好的表現。 新京報:“華中大”是一所理工科學校,你所說的“更好的教育”是否包括精神層面的東西? 李培根:當然包括。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講,不光是學習科技知識,還要修人文素養,要有超越于專業之外的社會、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及領悟能力。 新京報:而高校擴招是否會影響到你所說的“更好的教育”? 李培根:從宏觀上來講,前些年國家的擴招,我可以理解。一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對于人才的需求大;二是經濟水平發展,老百姓受教育的需求也增加。擴招是適應了這兩方面的需求,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擴招可能會引發一些教學質量下降的問題。 新京報:你的教育理念是反對高校擴招? 李培根:完全否定擴招,也是錯的,是不公平的。但我并不希望大學這么大。我的愿望是,希望這個學校能夠小一點。 新京報:為什么希望它小? 李培根:太大的話,教師跟學生的距離就遠了。學生越多,教師照應起來肯定就難一點。比如上一個實驗班,是50人來上,還是20人來上,差別就大了。 新京報:聽起來像精英教育,你希望在“華中大”提倡一種精英教育? 李培根:現在說“華中大”是精英教育,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們的學校,是介于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之間。 新京報:很多人說,中國的大學跟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不是一點半點,那“華中大”的差距呢?你希望把它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之一嗎? 李培根:當然希望,但我估計即使建成,也還要有幾十年。那時我肯定已不在位了。(朱柳笛 湖北武漢報道) 人物簡介 李培根 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曾擔任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院長、副校長。2005年3月起擔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6月23日,在華中科技大學2010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李培根的演講《記憶》打動了無數學子的心,并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 |